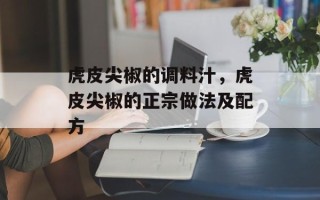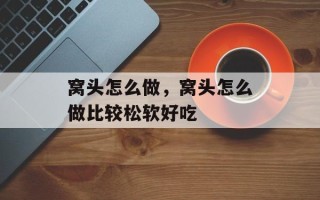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1282年-1284年期间,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扬州生活,并且谋了一份盐务的官职,领了元朝廷三年的俸禄。在进入扬州城之前,他自北向南来到了当时的高邮。这是一座地域广阔的城市,他对这里的印象是,“城市很繁华。民以经商和手艺为生,养生必需品俱极丰富,产鱼尤多,走兽飞禽各种野味皆甚多。用威尼斯银币一格鲁梭就能买到三只像孔雀那样大的稚。”
不仅如此,京杭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也让马可啧啧称奇——“注意了,我的读者客官,他们走的不是我们走的不是大海哦,是湖泊和河流啊!”
大运河畔的中国邮驿“活化石”
高邮,位于扬州市区北部,京杭大运河沿岸,高邮湖畔,东邻泰州市、兴化市,南连江都区、邗江区、仪征市。公元前223年,秦王嬴政在境内筑高台、置邮亭,故得名“高邮”, 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
到了明清时期,因盐业而兴的扬州一府置六驿,其中重要的两驿皆设在高邮,也让高邮的邮船漕运事业达到了顶峰。
高邮明清运河故道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孟城驿开设于明代洪武八年,是我国目前保存更好且规模更大的一座古代驿站。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由于南北两京并设,两地联系频繁,明运河沿线成为明代最繁忙的驿段之一,盂城驿的作用也更加巨大。据说,鼎盛时期有驿马130匹,驿船18条,马夫、水夫200人,房屋100多间,占地10余亩,堤上另建有迎饯宾客的皇华厅,东有秦邮公馆和饲养马匹的马饮塘。
孟城驿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俯瞰孟城驿 刘乐凯 图
不论酷暑严冬,还是狂风暴雨,传送重要急件的驿使都要快马加鞭,飞奔在尘土飞扬的驿道上。
如今,步入南门大街,在街道的尽头,可以看到孟城驿遗址。其中,正厅“皇华厅”,为一幢五开间明代建筑,是通邮传令,处理公文的场所,也是当时高邮州官接见过往使节的地方。
“驻节堂”是古代驿丞接待各路使节及四方宾客的场所,它也是整座孟城驿遗址上保存最完好的明代遗存,厅堂东西两侧为宾客的寝室,供官员下榻使用。另外还有“礼宾轩”,顾名思义就是接待官员的会客厅。
皇华厅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驻节堂 刘乐凯 图
为值更报时,报捷庆典,驿站还设有鼓楼,高约15米。站在鼓楼上,凭栏远眺,不远处浩浩荡荡的京杭大运河、巍峨的唐代镇国寺塔和水天一色的高邮湖美景尽收眼底。
鼓楼是驿站的标志性建筑。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1670年,蒲松龄作为同乡好友孙蕙的幕宾来高邮,曾驻留在孟城驿管理驿务,虽然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但留下《清水潭决口》、《早过秦邮》等诸多诗文,回忆自己在高邮的岁月。
1670年,蒲松龄作为同乡好友孙蕙的幕宾来高邮,曾驻留在孟城驿管理驿务。 澎湃新闻记者王昱 图
马可·波罗像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2013年,高邮市 *** 对孟城驿实施扩容,新建了秦邮公馆、客栈等建筑设施,并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区进行整治,打造了占地6600多平方米的特色景区。
2014年,高邮明清运河故道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孟城驿、南门大街、镇国寺塔等也都被囊括其中。
南门大街过去是丧服一条街,经过重修和改造,已经成为当地的历史文化街区
南门大街上的非遗展示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南门大街上的腰鼓队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双黄蛋、蒲包肉,忘不了的高邮味道
说到高邮,除了让马可波罗流连忘返外,还有一个人对高邮的感情也十分深厚。
中国当代作家、著名美食家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高邮的一个旧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文官,父亲也是位多才有趣之人,善绘画、喜弹奏、爱打拳、会烧菜。耳濡目染中,汪曾祺从小学习古文,能诗能画。
汪曾祺曾说:“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我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挑米、卖藕、孵鸡、贩骡、唱戏……他笔下的家乡充满了烟火气,充满了水乡柔情。而其中最少不了的元素就家乡的美食。
汪曾祺纪念馆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汪曾祺和妻子施松卿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双黄蛋是高邮最知名的特产,北宋文学家秦少游就曾以双黄蛋等家乡土特产寄赠师友苏东坡。而高邮双黄蛋到底哪里好?清代大文学家、美食家袁枚在其著作《随园食单》中解释道:“咸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
高邮的特产双黄咸蛋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高邮当地有一种麻鸭,体型大、身躯长、体格壮,不但本身肉质鲜嫩,所产的鸭蛋个头也大,双黄的几率也高。双黄鸭蛋大如鹅蛋,蛋壳质细、光亮,呈白色或淡绿色,在蛋壳外裹上一层黄泥和草木灰后,放入酒坛中腌制,大概3个月后,双黄咸鸭蛋就“出炉”了。
在《端午节的鸭蛋》一文中,汪曾祺不禁感叹:“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过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在蛋壳外裹上一层黄泥和草木灰后,放入酒坛中腌制。 澎湃新闻记者王昱 图
咸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 澎湃新闻记者王昱 图
在汪曾祺的小说《异秉》中,还有一道独具高邮特色的传统小吃频频出现。那就是“蒲包肉”。 据说蒲包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早期,距今已有300多年。蒲包肉的外形很奇特,看着像葫芦,被用蒲叶编织的“口袋”裹得严严实实的,根本不知道里面“卖的什么药”。
蒲包肉 *** *** 比较简单:把猪肉切碎,放入葱、姜、糖等搅拌均匀,再装入小蒲包中扎紧。然后把蒲包放入锅中,加入酱油、料酒、五香粉、桂皮、花椒、八角等焖煮一段时间即可。吃的时候,需要剪开外面的蒲包,但为了塑形,通常碎肉外面还会裹上一层豆腐皮,这样剥开蒲包的时候,一个完整的“葫芦”就出现在眼前,然后再切成一片一片装盘。
蒲包肉的外形很奇特,看着像葫芦。 澎湃新闻记者王昱 图
碎肉外面还会裹上一层豆腐皮,剥开后,一个完整的“葫芦”就出现在眼前,然后再切成一片一片装盘。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红白相间、有肥有瘦的猪肉带着蒲叶的清香,紧密有嚼劲,肉嫩弹牙。如今在汪曾祺纪念馆对面,有一家“二子蒲包肉”,据说《异秉》小说中“王二“人物的原型,就是这家老店过去的主人。
二子蒲包肉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图
汪曾祺不仅会吃还会做,“汪氏家宴”就是他发明的。他常在家中招待客人吃的菜肴,其中大多以高邮的特产为原料,例如咸菜慈菇汤,高邮的咸菜一般是用瘦长的大棵青菜腌制的,腌到菜梗子黄黄的,甚至透明,口味更佳;还有虎头鲨汆汤,汪曾祺说苏州人稀奇的虎头鲨,在高邮最平常不过,而且高邮的虎头鲨肉细不散,味道极鲜。
美丽的高邮湖 澎湃新闻记者王昱 图
高邮滨湖临水,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水而兴。而这座古老驿站,永远等待着新的探险者到来。
责任编辑:徐颖
校对:张艳
韦小宝骂吴三桂是高邮咸鸭蛋,汪曾祺听了作何感想?先给大家破个谜语:
“这道美味很普遍,家家餐桌都曾见。出产之地在江南,信手拈来骂han奸”
看过金庸先生《鹿鼎记》原著的朋友,相信一定很容易猜得到。
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扬州人吗?”韦小宝道:“正是。”吴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辽东,原籍扬州高邮。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韦小宝心道:“辣块妈妈,原来你是高邮咸鸭蛋。扬州出了你这个大汉奸,老子可倒足了大霉啦。”
那天浏览某宝,无意中看到“高邮咸鸭蛋”,不由想起《鹿鼎记》中这段情节,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县不在大小,有蛋就灵。
很早就读过汪曾祺《端午的鸭蛋》,他的家乡是水乡高邮,目前为江苏省一个县级市,高邮 *** 鸭是著名的鸭种,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汪一对别人提起自己家乡,别人都肃然起敬,反倒弄得他很不高兴,觉得好像他家乡,穷的就只有鸭蛋。
不过高邮咸鸭蛋确实出名,50年代,一曲高邮民歌《数鸭蛋》,以其诙谐、轻快的旋律,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声震京都,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赞誉。高邮鸭是高邮人的名片,"未识高邮人,先知高邮蛋"。北宋著名词人秦观,也曾以鸭蛋馈赠其师友——时任徐州太守的苏东坡。清代大文学家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中也留下了记载:"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
高邮鸭蛋如此出名,但以前却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毕竟鸭蛋是很常见、很廉价的东西,没人会把其当一回事,而母亲却常跟我提起,她幼年时端午节吃咸鸭蛋的故事。
那是60年代物质相当匮乏的时期,但她所生活的乡间,还算勉强可以,端午又是与中秋、春节并列的三大重要节日,因此一早起来,饭菜就相对丰富,白米粥、粽子,就着自家种的青蒜、生菜,蘸着鸡蛋酱吃。酱也是自家腌制的,平时多生吃,端午却要专门用鸡蛋炸熟。之后,姥姥还会煮上一大锅的鸡蛋鸭蛋,都是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然后给孩子们每人分上三个鸡蛋、两个鸭蛋,当做节日礼物。
之后就有趣了,母亲他们几个兄弟姐妹,有的把蛋藏在板柜里,有的藏在被窝里,有的藏在草垛里、还有藏在鸡舍里的,大家这时免不了斗智斗勇,彼此猜测对方藏蛋的地点,也有直接开口讨要的,看平日手足相处的情份了,谁若是能想办法顺走,或多要到一枚两枚,就像占到了极大便宜似的。虽偶尔会闹出小摩擦,但那时的孩子们都很懂事,也都手足情深,基本不会把事情闹大。不像我,自幼为独生子女,从未体会过手足之情的滋味,所以,每每听父母讲起这类事时,都会觉得很羡慕,也很向往。
*** 时代到来后,也邮购过高邮咸鸭蛋,但不知是否因没买到正宗的,还是现代人口味太刁,并没吃出什么太让人难忘的味道,感觉跟我们本省白洋淀出产的相比,也没什么不同。
其实,在物质条件如此丰富的现代社会,没人会将这种普普通通的食物当作一回事,只有将其拿到母亲面前时,才可能又勾起一波老人的回忆杀,虽然之前已讲过多次,但她仍会不厌其烦地再给我讲一次幼年端午吃鸭蛋的故事,因为,故事里饱含着她对逝去的父母、兄姐间的满满思念之情。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角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种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 *** 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枚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邮之信,不死必达未识高邮人,先知高邮蛋
很多人知道高邮,是因为一枚鸭蛋,尤其是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是别处的鸭蛋难以匹敌的诱惑。
如果你们遇到一个高邮人,想必也会像我一样脱口而出:“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而高邮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城,可不是一枚小小的鸭蛋能讲清的。
高邮之得名
细细想来,中国好像没有哪个地方是以“邮”字命名的,高邮,是独一份儿。
高邮这个地方,“襟带苏皖、控引下河”,地理位置十分紧要。
秦朝时,秦王嬴政便瞧准了这个地方,为巩固政权,便在此地筑高台,置邮亭,“高邮”之名由此而来。
古往今来,无数信件、文书经由城内的驿站转送,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名。
古代的邮驿有多牛
高邮古城中的盂城驿,始建于明洪武八年,是今天中国保存较为完好的古驿站之一。
在过去,驿站乃是官办机构,功能配置那叫一个齐全,人手安排也是细致得紧。
比如说,驿站的更大长官叫做驿丞,负责管理驿站所有事务;驿丞的副手叫做攒典,相当于县衙的差役;再下面还设有棚头、差头、马夫、水夫、旱夫等角色,最宏伟的时候,工作人员能达到199人。
历史上,驿站有着“国之血脉”之称,承载着沟通南北、传达政令、飞报军情、转运军需、迎来送往的重大使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和南京的联系依然紧密得很,六部人员都留守在南京,所以两地之间的公文、书信那是一封接一封。
由此,从南京经大运河转运北京的水陆邮驿,便成为了重中之重、要中之要。
当时南京、北京之间,共设有46座水马驿站,形成一张巨大的邮驿网。
其中高邮的盂城驿,管理着15个传递公文的急递铺,采取“常事入递,重事给驿”的管理模式。
常事给递,就是平常的信件通过步行送到基层;要事给驿,则是通过快马传递重要公文。
邮驿之要在于争分夺秒,每座驿站的庭院正中都会设一日晷,它是衡量驿卒时效的标尺。日晷分12格,一格代表两个小时,12格就是24小时。
那时候送信的快马,一般一天可行300里,最快可达到800里。
打个比方,南京到高邮相距大约340里,如果用一匹跑800里的快马来跑的话,只需要半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日晷走半圈,驿卒的信件就会送达。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是古代邮驿工作的真实写照。古代邮驿 *** 的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在明朝时达到了顶峰,京城政令一经发出,60天内便可通达全国各地。
高邮古城的驿卒们就这样,在与时间赛跑的日子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明清时起,高邮城发展至鼎盛,经由京杭大运河往来此地经商游历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百姓传递书信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城内从事邮驿行当的人家也越来越多。
古城人常说,“行船走马三分命”,意思是只要选择邮驿这个行业,就会面临无数风险。
明永乐年间,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生命垂危之时,她托驿站水手杨仲礼把家里的田契,带给远在南京谋生的儿子。
老人家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上“珍重”二字,郑重交到了杨仲礼手上。
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行船至长江。不料,当航程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携卷着巨浪拍打着船身,杨仲礼不慎落水。
落水的那一刻,杨仲礼的之一反应就是紧紧抓住盒子,尽管一只手抓着盒子,一只手游泳,是十分费力的,他也始终不肯把盒子丢掉。
当人们将杨仲礼搭救上来,已经昏迷的他依然紧紧抓住包裹,掰都掰不开。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但他手中那封沉甸甸的田契,却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那个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一封家书,一旦背到了他们肩上,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邮之信,不死必达
走过烽烟岁月,来到现当代,虽然古驿站早已被现代邮政系统取代,但留存在这座千年邮都的重信守诺之风却始终不曾改变。
杨永福是一名退休的邮差,他在邮政行业服务了四十多年,当时他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转送机要文件的工作,每天跑一百多公里是他们的日常,刮风下雨也是如此。
1965年的一天,杨永福在骑车送信途中,突然下起暴雨,雨势异常猛烈,被雨水模糊视线的杨永福,没能看到横在巷子里一根被风刮倒的电线,脖子上被割出一道深深的伤口。
但那时,杨永福之一时间想到的却不是去医院处理伤口,而是不能耽误送信时间。
他一只手捏着脖子,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手,冒着暴雨继续前行,直到将文件安然送到目的地后,他才放心地去了医院。
医生告诉他,差一点点,他的嗓子就断了。
但在杨永福心里,将文件安全送达,就是他的首要任务,其他都是次要的。
他们身上担负着使命,有的是军情,有的是调价信息,时效性很强。比如今天的调价信息,明日才送达,库存量就不一样了,国家和人民就会受损。
邮之信,不死必达。古老的邮驿文化,培育出了高邮人重信守诺的淳朴民风,也续写着“东方邮都”的传奇。今晚20:00,锁定CCTV-4,走进高邮古城,见证“东方邮都”的传奇故事。
《记住乡愁》第七季
播出内容:《高邮——东方邮都》(上集)
播出时间:2021年1月6日(周三)20:00
播出频道:CCTV-4 中文国际频道
编辑 | 王琳艳
在江苏省扬州市下辖区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就是有着东方邮都之称的高邮市。可能大部分人对于高邮市的认识都来自于高邮咸鸭蛋,那是汪曾祺先生笔下端午的鸭蛋,高邮端午习俗与外地相似,贴五毒,喝雄黄,尤其是高邮 *** 鸭产出的高邮咸鸭蛋,多双黄蛋,油多味香,是端午必不可少的美味。时间久了,似乎关于高邮这座城市唯一能与之产生联系的便只有咸鸭蛋了。
但这座名气不大的小城,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高邮有着东方邮都之称,留存在高邮的盂城驿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邮驿站。高邮见证着中国千年邮驿历史的发展。
高邮还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地处江苏省中部,有着7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和2000多年的建城史。京杭运河高邮段成为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也是高邮市水运历史的佐证。高邮湖、澄潼河、龙须沟、人字河等19条河流,为高邮这座水乡平原提供丰富水资源,富庶了千百年的江南水乡之城。
之一次来到高邮市,去到盂城驿,去了解古代中国的邮寄历史,在没有现代物流的时代,往返于京城与江南的邮驿,必定经过高邮邮驿站。再来逛逛南门大街,当地的早市,街道保留着古色古香的江南韵味,买两个咸鸭蛋,颗颗都会流着红油。之一次尝试当地特色的蒲包肉,口感紧实,鲜香可口。酥糖、茶干、酱油面……高邮这座城市在保留传统韵味这件事儿上真正做到了古法传承,总有许多地道的特色流传了千百年,至今还是为人称道。
世界遗产城市、历史文化名城,这些美誉似乎都融入了高邮的血脉之中。沿着京杭大运河逛逛,世界遗产就如此安静的流淌着,逛逛千年历史的南门大街,古色古香的老街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情。正值端午时节,家家户户包粽子、挂艾草,当然最不能缺少的还是高邮咸鸭蛋。
今天,“被语文书安利过的东西”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网友纷纷提名:高邮咸鸭蛋、《我的叔叔于勒》中的牡蛎,《社戏》里的水煮蚕豆……
高邮咸鸭蛋出自汪曾祺《端午的鸭蛋》,文中描述“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网友评论:
“我对咸鸭蛋的执着就来自汪老先生!”
“汪曾祺真的适合写一本美食攻略!”
《我的叔叔于勒》中的牡蛎也让很多人记忆深刻:
“她们的吃法很文雅,
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
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
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
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网友评论:“那个牡蛎,上着课就流口水了”、“这篇课文来来去去看了十几遍”
那么悲伤的故事,你们却只记住了牡蛎多好吃!
鲁迅的《社戏》也是高票当选,文中写偷吃罗汉豆。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鲁迅也是妥妥吃货一枚啊,孔乙己的茴香豆、月下的西瓜、三味书屋里的覆盆子、何首乌……鲁迅说过哪些话忘了,这些倒记得牢牢的。
其他提名还有:
@别吻我臭流氓:荷塘月色,每次洗完澡就感觉自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花
@不能让人发现逛窑子的小号:我还记得槐花五月那节课上完,我们学校的槐树上爬满了同学
@一只特立独行的蹄:火烧云 !!!萧红的那一篇“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
@王大暿:东坡肉!我还特地照着语文书做了一遍,真的巨好恰!
你还被安利过哪些东西?在评论中留言。
zaker潇湘综合
汪曾祺: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作者 |草湖的雪(孔网店铺:草湖书屋)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好多年前读了汪曾祺先生《端午节的鸭蛋》后来在某东上看到高邮的鸭蛋有售,就买回来尝尝。
汪先生是这样描述他家乡的鸭蛋的:“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
汪先生的描述没有广告来的直观,广告上配有图片,那个图片比真鸭蛋都诱人。不过,说实话,高邮的鸭蛋的确不错,但大家都清楚不是每个鸭蛋都是上品。
生活中各种可能都会发生,汪先生用平常而又不平淡的文笔表达了一种生活态度,豁达,宽容,大度,让人敬仰。
作者:董兆林
手边有本《汪曾祺散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散文珍藏版”丛书中的一种。这是第二次阅读了。有的书就是这样,读过之后还想再读。比如《红楼梦》,真正喜欢的人恐怕不会读过一遍就拉倒了。
再读《汪曾祺散文》,我对他记述美食(吃食)的那些篇章有了兴趣。这绝非以标榜什么“吃货”为时髦,而是自不量力想从中辨析汪先生文中的一点小瑕疵。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无华丽的辞藻,走笔行文就是那些寻常字、普通词,但这些字词组合起来,便别有韵味,平淡之下透着清雅干净,意味深长。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总觉得文字词浅意深,不由让人慢慢读下去,或许正如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中所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再翻这本散文集,方察觉汪曾祺的散文,有不少篇什都涉及“吃”:有的是专门谈美食,有的是在谈论别的话题时,飨食只是顺笔提及,蜻蜓点水。如写《观音寺》时,点缀一笔西南联大的女同学爱把昆明的胡萝卜当水果吃,因这种细嫩微甜水分多的胡萝卜,既便宜又驻颜;写《跑警报》,当日军敌机来袭,小贩们索性也和联大的师生们一起跑,躲避空袭时顺带还卖些麦芽糖之类的零吃;《随遇而安》中,当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到张家口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画《中国马铃薯图谱》——画叶子,画剖面,当完“模特”的马铃薯最后的使命是埋身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汪先生应该是吃过最多品种烤土豆的人。还有《老舍先生》中那让人馋涎欲滴的芥末墩……
我有些迟疑的是《吃食和文学》中的一章:《苦瓜是瓜吗?》。
有一次,汪曾祺请来北京出差的同乡吃饭,席间有一盘炒苦瓜。同乡夹了一片入口,味苦,不禁问道,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汪曾祺说:“酸甜苦辣咸,苦也是五味之一。”又告诉他们:“这就是癞葡萄。”
其实苦瓜并不是癞葡萄。从外在看,二者的表皮都有些疙里疙瘩,但苦瓜细长,癞葡萄呈团形,像手雷;苦瓜是菜蔬,癞葡萄是水果。由此我想起一件旧事: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下班给我拿来两个金黄色的癞葡萄,大概是厂里南方的工友探亲带回来的吧。在北方这可是个稀罕物,掰开疙疙瘩瘩的果壳,里面挤满了鲜红多汁的籽粒,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包裹着籽粒的果肉味道甜美。当年学校兴起一股种蓖麻热,各年级各班在学校围墙边都种。我突发奇想,留下一枚吃剩的果核,打算种癞葡萄。种子埋到自家院子里那棵香椿树下,一周后竟然见芽,后来顺着篱笆慢慢长出藤来。我欣喜若狂,每天放学后都要照料一番这枝“奇葩”。最终,爬在篱笆上的枝蔓藤上还真结出两粒果实,引得街坊四邻都来围观,啧啧称奇。后来才知道,癞葡萄也叫“金铃子”。这个名字好听。
读书勾起少年时的一段往事,也算是个收获吧。
再回到书中,汪先生有篇《我的家乡》谈的是高邮的世态风情,结尾仍不忘写上一笔吃食。高邮的 *** 鸭很能生蛋,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邮咸蛋”,且双黄者居多。久而久之,人们似乎只记得高邮的咸鸭蛋了。为此,汪曾祺调侃道:“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秦少游……”读到此处,不禁令人莞尔。(董兆林)
“咸蛋”还是“咸鸭蛋”,“小棠菜”还是“小藏菜”?|李荣“咸蛋”还是“咸鸭蛋”?
汪曾祺先生曾为别人的一本书做了一篇序文,最后有一句“上海卖咸鸭蛋的店铺里总要用一字条特别标明:‘高邮咸鸭蛋’”。序文寄出后,汪先生追了一封信去,信中说:“(那一句里)‘鸭’字不要。上海人都说‘咸蛋’,没有说‘咸鸭蛋’的。想来是抄录时加了一个字。”
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西南联大毕业后,曾经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两年左右,与黄裳先生和黄永玉先生等好友时相过从,对于上海多少有点“发言权”。他后来那封信里言“上海人都说‘咸蛋’”云云,大约即是当时身在上海由市井见闻中所得到的印象和记忆吧,因为是直接的,而非听人转述或者书本上看来的,所以说得很是肯定。
我自小一直生活在上海,六十年代出生,所以四十年代上海人如何称呼“咸蛋”,我没有直接的知识。但是,我家里的老辈,比如我的老阿奶,嘉定黄渡人,她的上海话应该是“原汁原味”的。她说“咸蛋”,但也说“腌鸭蛋”。只要是吃泡饭(吃剩的干米饭加水烧成)或者“新鲜粥”(直接用米粒加水“新鲜”煮成)的时候,常常会问一句:“要不要来一只腌鸭蛋?”此外,说上海话的亲戚朋友,称“咸蛋”为“咸鸭蛋”的,也很多。
不过,汪先生的想法也有他的道理。把“咸蛋”说成“咸鸭蛋”,多少有点多此一举,因为用来腌成咸蛋的,基本上都是鸭蛋。“咸鸡蛋”“咸鹅蛋”,当然不能说是绝对没有,我就听说我太太的一个同学好奇心强、也喜欢做厨房里的“创新之举”,有一次便尝试用鸡蛋来腌成咸蛋。我没有亲口尝过这样的“创新成果”,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但听转述,滋味没有咸鸭蛋好。这首先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吧——吃惯咸鸭蛋,难免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咸鸡蛋”的味道,觉得不像就肯定认为不如了。
但是仔细想想,鸡蛋与鸭蛋相比,蛋白蛋黄都要嫩得多,腌成咸蛋“吃口”就会比较弱一点,而且鸡蛋日常的用量大,烹饪法多种多样,以鲜嫩的吃法为主,腌成“咸蛋”,有点“浪费食材”的意思了;而鹅蛋与鸭蛋相比,质地更为粗笨,腌作咸蛋的话估计吃起来腥味较重,除非口味比较奇特的,一般人大概有点受不了。所以“咸蛋”这个称号才成了咸鸭蛋的专称了。汪先生当时印象里上海人只叫“咸蛋、咸蛋”,应该也是出入不大的。
上海人吃咸蛋有几种吃法。一种是一只带壳的蛋,对切成“两爿”或者再对切而成“四爿”。这种吃法要么是家里人口多,切开来吃,大家都有份,人人都可以吃到;要么是家里摆桌头,用来装一只冷盆,排列开来看起来好看一点;要么就是有的人家“吃口”偏淡的,一人吃整只蛋嫌太咸了,切开来分个几次吃。还有一种吃法是把咸蛋的壳整个剥干净,放在泡饭或粥里吃,但这样吃法的人应该不多的。
我所最喜欢的吃法,是拿起咸蛋,对着光亮处照一照,看见蛋的内部哪一头隐约有一点空的地方,便用这一头对着桌面轻轻地把蛋壳敲开,剥出一个小“开口”,用筷子慢慢地挖着吃。最要注意的是之一筷戳下去,不能用力过猛,否则,如果咸蛋质量好,油多,一用力,油便会挤崩出来,不单单自己弄得“油头油手”的,不凑巧还会溅到旁边人的衣服上,抹不了、擦不净,那就有点恼人了。只要这个起头照顾到了,那么蛋白蛋黄“搭配”着吃,一小筷子咸蛋的滋味可以“下”好几口的白粥。一只蛋吃光,一大碗热粥也就下肚。热热乎乎,清清爽爽,口有余香,真是不错。尤其前不久发烧退热之后,就想着可以吃一顿粥了,再加一只咸蛋。
从小听惯的老阿奶嘴里的“小藏菜”
我现在遇到有关上海话上的问题,常常会请教褚半农先生,但彼此只是微信问答,到现在还没有见过面,他惠赐了他的《莘庄方言》等好几本大著,让我受益不小。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在“初识”之前,褚先生通过文汇报笔会版的“回音壁”专栏,还曾指教过我文章中一处存疑的地方。
那是我谈论《清嘉录》里有关“叫嗓子”的一篇小文,我说“叫嗓子”有点像含在嘴里的“哨子”。哨子上海方言里称“叫bian”,这个“bian”音,到底落在哪个字上,我确定不了。直接想到的,就是“叫鞭”,但难以自信。于是便去问了另一位上海话的研究专家,他说应该是“叫扁”,因为它的形状是扁扁的。我想应该有道理吧,而且他又是专门家,所以在文章里便写为“叫扁”。文章在笔会上登出来了。笔会有一个好传统,专设一个“回音壁”栏目,专门登载读者来信,指正副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疏失。一段时间以后,“回音壁”上便有了褚先生针对我那文章的“回音”,认为应该写为“叫鞭”,而且引用了不少的证据,说服力不小。
最近,看到褚先生新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到上海本地话,叫青菜为藏菜。一下子让我记起,我家老阿奶过去一直把小青菜叫做“小藏菜”,音完全对。但是如今普通最常见的写法,却是“小棠菜”。音近,但与老上海的发音,还是有距离。记得在沪郊采访的时候,还听过这么一种解释:“小藏菜”是肖塘菜,因为奉贤肖塘是菜乡,青菜出名。但我感觉这应该是不正确的。
我给褚先生发了一条微信,说了我的一些猜想,大致有三种可能:
一是藏菜之藏,是因为藏青色,由青而藏,连类而及。我们从小在上海吃到的青菜,好像有一种,是深绿甚至偏紫的菜种。或许藏菜是指的这一种,亦未可知。
二是古籍里的藏菜。《古今图书集成》中云:“藏菜即箭秆菜,经霜,煮熟甚美,冬日腌藏以备岁,故名。”徐光启《农政全书》列于“芸苔”之下曰:“藏菜七月下种,寒露前后治畦分栽,栽时用水浇之,待活,以清粪水频浇,遇西风则不可浇。”《姑苏志》云:“藏菜出郡城,肥白而长,名箭干菜。冬月腌藏以备岁,故名。”《江南通志》云:“箭杆白菜,菘之属也。取其中心嫩芽以为羹,味甘美绝伦。其外大茎叶以盐腌之,可以御冬。正月食之,尤香脆,吴下谓之藏菜。然不若江宁郡城者之佳也。”
从这几条记载来看,藏菜又名箭干菜。由这“箭干”的取名而言,应是形容这种菜的形状是长长的。不同的记载,归其种属亦有不同。《农政全书》归在“芸苔”类,那便是油菜,油菜籽可榨油,但有些品种的油菜,其细嫰的茎叶亦可作菜蔬食用。而《江南通志》则归之为“菘之属”,菘是白菜类,江南的青菜,正是一种小白菜。这里便有一点“混乱”。不过,上海人历来的食用菜蔬中,有青菜,也有一种叫“菜剑”,老人有时候直接就叫其为“油菜”。我自己小时候,看到大人买菜回来的菜篮头里有这样的油菜,菜头上还有几小簇黄黄的小花,就会摘下来放在小口瓶里,灌满水,花也会渐渐开放,足有好多天可供赏玩。
那么,在“一个菜篮”,有时候青菜、油菜“混说”了,也有可能。只是这一个“藏菜”的称呼,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可以腌渍以后囤积起来过冬,供新鲜蔬菜少的季节来食用。早在《文选》的注文里,就有“藏菜曰菹”的说法。《释名》云:“菹,阻也。生酿之,遂使阻于寒温之间,不得烂也。”
最后一种可能,即是“存其音”而已。如果只是记其音,那么可用“藏”,也可用其他同音的字,比如“小棠菜”,都无不可了。这样,便不能从“藏”字本身来定其意思。不过,这个音的后面总应该还有“东西”,由其音去联想,这还是一个未解的“尾巴”。
让人感动的是,褚先生接到我的微信时,尚出门在外,不仅马上回复了,而且答应一回到家,就把他手头有的资料发送过来供我参考。他认为,藏菜名的书写,至少有常菜、上菜、塘菜、棠菜、床菜等好几种,其实都是“语转词”。这是因发音变化和对传统词语缺乏了解,方言书写中出现的“语转词”,即声音稍有变化写出来变成另一个词,成异形词。青菜、藏菜名的记载,从地方志看,非常复杂,也非常混乱。这同先前的文言记载过分简单、没有图示,以及后来的人不熟悉农作物有关。
这些意见,我觉得都很中肯。知堂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起过:“清季的学者张啸山在笔记中曾叹说,读《诗经》《尔雅》,不明白那些动植物是什么形状,看见了实在的东西,又不知道他在书上是什么名称。这两句话很能说出向来研究名物的缺点。孔子教人学《诗》,说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后来学者便忠实的这样做去,记住了好些雎鸠卷耳的名字,及至见到了他们却又对面不相识,也并不想认识他们,但是著作起来可以写成整本的书,引据渊博,我们外行人看了还是不得要领。”
所以,唯一可取的办法,首先是取一个“集注”的态度,把那些“混乱”都一一摆出来,然后再一一梳理一下,当时古称的东西,即是如今的什么,然后回过去再看古称之来由,那便极有乐趣。还有各种混说“致乱”的原故,那里面也有不少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人们的观察、认识和生活细节,即便张冠李戴是错误了,而一旦整理清楚了,却也是愉快的。
<南风之薰>是李荣在笔会的专栏
作者:李 荣
编辑:钱雨彤
汪曾祺——端午的鸭蛋摘自《文人与故乡》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角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么?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 *** 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有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
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作“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小时读囊萤映雪的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