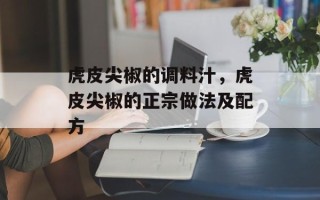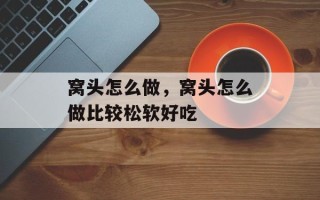屠呦呦团队青蒿素研究的应用普及的合作对象,为何是昆药集团?
6月18日凌晨,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药集团,600422)在其官微发布名为《昆药集团:与青蒿结缘 创造生命奇迹》的文章,详解了该公司有关参与青蒿素抗疟药研发、生产的历史。
“作为全球之一家青蒿素生产企业,昆药集团有幸与屠呦呦团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携手合作,参与并见证了青蒿素的全球普及之路,并持续在抗疟领域及新适应症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及探索。”昆药集团如此表示。
官网资料显示,昆药集团的前身为成立于1951年3月的昆明制药厂,2000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昆药集团集药物研发、生产、销售、商业批发和国际营销为一体,形成了以自主天然植物药为主,涵盖中药、化学药和医药流通领域的业务格局。
此前一天的6月17日,据新华社报道,由屠呦呦团队所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交的“双氢青蒿素片剂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盘状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已获批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负责单位开展临床试验。记者了解到,临床试验一般共三期,二、三期试验样本量更大,至少还需7到8年。若试验顺利,预计新双氢青蒿素片剂或最快于2026年前后获批上市。
6月17日晚间,昆药集团公告称,公司目前销售的青蒿素类产品用途均为疟疾治疗,且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公司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目前尚处于临床二期患者入组阶段,该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世纪60年代就曾参与研发抗疟药
昆药集团研制抗疟药的时间比较早,根据昆药集团的介绍,20世纪60年代,中国启动了一项代号523的项目,该项目动用了超过60家科研机构及大约500名科学家,旨在研发一种新的抗疟疾药物。当时,昆药集团的前身昆明制药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企业,参与了此项研发工作。
在1979-1983年四年的时间里,昆药工作人员进行了数千次的实验,并对各种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1984年,昆药成立了中试车间,经过8年时间,1987年,国家卫生部批准了昆药生产青蒿素的衍生物:蒿甲醚原料和蒿甲醚注射液两个一类新药。
1990年,昆药集团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携手联合研发蒿甲醚复方型抗疟特效药,形成著名A+B新复方,该组方是全球之一个ACT固定比例复方药,开创了ACT药物开发及应用的先河,昆药成为全球之一家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进行疟疾治疗 *** (ACT疗法)研究的企业。
除了研制抗疟药的时间比较早,昆药集团还追溯了对复方蒿甲醚的研究过程。
1987年,昆明制药厂与军科院五所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发复方蒿甲醚,并于1992年获得我国新药证书。1998年,复方蒿甲醚以商品名“Coartem”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中国原创新药取得国际专利的先例。
2004年,昆药与军科院合作,研制出新一代复方抗疟药ARCO(复方磷酸萘奈酚喹片),首次实现单次片口服即可治愈非复杂性疟疾,成为全球之一家推出一次服药就可治愈的抗疟药品种。
“目前,昆药集团拥有七个蒿甲醚系列产品品种,参与起草制定的5个蒿甲醚系列药品质量标准(青蒿素、蒿甲醚、蒿甲醚片、蒿甲醚胶囊、蒿甲醚注射液)收载于国际药典标准。其中,生产的复方蒿甲醚系列药剂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抗疟药,其针剂主要出口南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同时蒿甲醚等抗疟制剂已在全球35个国家登记注册。”
昆药集团在官微文章称,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未来昆药将持续投入更多资源和力量,继续推进青蒿素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并以优势产品和技术为主导,加强与各大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合作,引进国内外优质资源和人才,把更多的优秀药品推向世界。
2018年抗疟产品仅占营收0.98%
昆药集团在6月17日的公告中表示,公司在售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产品有:复方磷酸萘酚喹片、蒿甲醚片、蒿甲醚原料、蒿甲醚注射液、双氢青蒿素哌喹片。
但从业绩贡献来看,昆药集团上述抗疟药产品的营收占比并不多,此类产品2018年营业收入为6,925.92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比例仅为0.98%,营业利润为667.65万元,对昆药集团业绩影响较小,昆药集团所销售的上述青蒿素类产品用途均为疟疾治疗。
关于最受关注的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研发进展情况,昆药集团表示,2016年9月8日,该公司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签订《双氢青蒿素片新适应症-红斑狼疮项目 *** 合同书》,以里程碑付款的方式,出资7000 万元,向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购买其所持有的双氢青蒿素片新适应症-红斑狼疮研发项目临床前研究所取得的相关专利及临床批件。
昆药集团解释,目前上述研发项目处于临床Ⅱ期患者入组阶段,这个药物研发项目还需要继续进行二期临床试验、后续还需要III期临床试验,以及药监局的注册审批程序。只有在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均表明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后,公司才可以向药监局(NMPA)提交新药注册申请。
“药物研发的二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及注册时间很长,而且在临床试验以及注册申请的过程中,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能否得到验证,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该项目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的风险。即使药物能上市销售,仍然面临专利保护到期,竞争品种抢占市场先机等系统性风险。”
最后,昆药集团提醒投资者,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月17日,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药集团,600422)开盘以一字板涨停,报9.69元/股,封单超过100万手。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青蒿素制剂再获突破来源:经济日报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分散片、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片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药品预认证(WHO-PQ)。其中,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分散片为首个适用于儿童的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类剂型。
疟疾与结核、艾滋病并列为世界三大传染病,全球约有半数人口面临疟疾风险,其中多数感染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长期以来,疟疾均为导致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017年,全球预估有2.19亿例疟疾病例,43.5万人死亡。疟疾通过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在人群中传播,人一旦感染后,将出现发烧、寒颤和呕吐等症状,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措施,病情进展为重症疟疾后将引发贫血、昏迷、多脏器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目前,青蒿素类抗疟药品主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 *** 基金等采购。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7年,全球共采购青蒿素类复方药物约27.4亿人份。
自2000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推荐使用含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复方药物ACTs用于无并发症疟疾的治疗。2005年,世卫组织发布之一版《疟疾治疗指南》,列出了4个含有青蒿素衍生物的复方口服制剂。2010年更新后的第二版《疟疾治疗指南》中列入第5个复方青蒿素类口服制剂——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片。2015年,世卫组织第三版《疟疾治疗指南》根据最新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成果调整了该药物的用药剂量,从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而复星医药研发生产的两种药品,是市场上最早采纳这一新剂量的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产品。如今,适用于儿童的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类剂型通过WHO-PQ认证,将成为非洲抗击疟疾的又一重磅武器。
在疟疾流行地区,儿童、老人等易感人群在疟疾高发季节可反复感染疟疾。ACT类复方药物将快速起效的青蒿素类药物和一种持续起效的长半衰期药物联用,可在药物半衰期内预防患者再次感染。而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片的长效活性成分磷酸哌喹半衰期长达11天,可为患者提供更长的保护期。
目前,复星医药的创新药——注射用青蒿琥酯Artesun?,已经是国际上治疗重症疟疾的金标准。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通过WHO-PQ认证以来,已向国际市场供应了超过1.2亿支注射用青蒿琥酯,帮助全球2400多万重症疟疾患者重获健康。
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是什么?治什么?5个问题告诉你答案6月17日,根据媒体报道,屠呦呦团队将发布“重大突破”,导致昆药集团迅速涨停,但屠呦呦团队随后回应称,对红斑狼疮的研究并不是重大突破,而只是最新进展。
这是西南证券医药团队2015年10月的关于青蒿素的研报内容,由朱广国团队撰写,其中一些要点可以科普屠呦呦与青蒿素的相关知识。
一、青蒿素是国际抗疟首选药
2015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中,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的对抗疟疾的青蒿素举世瞩目。屠呦呦女士从1969年开始研究青蒿素类药物,在研究黄花蒿抗疟效果的过程中得到了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改换了提取方式,于1972年成功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有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青蒿(Artemisiaannua)是一种菊科植物,长久以来以其退烧的能力而闻名。上世纪90年代的加纳,治疗疟疾仍普遍采用奎宁,但这种药物对肝肾功能损伤较大,且现阶段疟疾寄生虫对大多数抗疟疾药物都产生了抵抗力。
青蒿药物是目前抗击疟疾的最有效药物。其发明带动了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为当前中国被国际承认的唯一创新药物,当前已经成为国际抗疟(疟疾)首选药。
屠呦呦女士在诺贝尔奖上的成就实至名归。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2000-2013年间,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47%,约430万人免于死亡。其中,青蒿素类药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青蒿素源于中药,但属于化药
青蒿素和中医药的联系确实非常紧密,但是它的研发过程与传统的“煎煮熬”完全不同。其为研究人员参照古今医书的记载和民间用方,用现代的研究 *** 对数千份植物提取物通过动物筛选,再从中分离、鉴定其中抗疟有效成分,最后找到近十种抗疟有效单体,将它们的抗疟活性、毒性、化合物稳定性和资源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后得到,有明确的分子式。
这就意味着它遵循了现代药理学和化学的 *** ,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提纯-再试验-测定化学结构-分析毒性药效-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提取工艺优化-生产工艺的制药流程,且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临床试验中也全部使用了双盲法,这和传统 *** 有很大区别。在CFDA的批文中,青蒿素属于化药。
在抗疟市场上,青蒿素的运用主要通过三个衍生物实现:蒿甲醚、青蒿琥酯和双氢青蒿素。而且,为了避免耐药性的发生,WHO于2006年要求立即停止提供单剂青蒿素疟疾药片。
目前市场上运用的青蒿素制剂均是复方,主要有5个复方被建议使用:1)蒿甲醚+本芴醇;2)青蒿琥酯+阿莫地喹;3)青蒿琥酯+甲氟喹;4)双氢青蒿素+哌喹;5)青蒿琥酯+磺胺多辛-乙胺嘧啶复方片。
三、全球青蒿素制剂市场容量处于收缩状态
根据WHO统计,全球约32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危险中,2013年约有1.98亿疟疾病例和58.4万死亡病例,90%疟疾死亡发生在非洲。
非洲地区的青蒿素类药品主要由WHO统一采购发放。若按2013年疟疾病例数计算,复方青蒿素药品需求量约2亿人份(一人份即一位患者5天的用药量),按平均每人份2美元成本计算,我们估计全球青蒿素类药品市场容量约4亿美元。
但WHO表示,随着疟疾防控措施的增强,疟疾防控已取得显著进步。自2000年以来,疟疾死亡率在全球已降低47%以上,世卫组织非洲区域降低了5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增加了43%,但每年感染疟疾人人数反而减少,从2000年的1.73亿减少到2013年1.28亿。因此我们预计全球青蒿素类药品市场容量处于收缩状态。
四、制剂市场:国内企业与之失之交臂
由于抗疟药的销售市场主要在非洲等世界穷国,这些国家本身需求能力有限,供给来源主要来自于WHO的统一发放。而国内的药品要销售出去又几乎得依靠 *** ,层层倒手之后药价已经大幅提高,因此,WHO采购为青蒿素类药物放量的主要途径。
而遗憾的是,由于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中国在青蒿素的产业化过程中却落入了国外的专利壁垒中。在专利、资金等因素下,中国原研的青蒿素类药品并未成功走向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有制剂产品通过WHO的PQ认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药品研发者和制造者们与西方同行展开合作。
1988年,桂林制药厂与赛诺菲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其提供青蒿素产品;1994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将青蒿素类复方药物的国际销售权出售给瑞士公司Ciba-Geigy,该公司后来成为诺华制药。
1999年,诺华成为全球之一家推出固定剂量复方蒿甲醚的制药公司。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之一款复方蒿甲醚时的合作伙伴——昆明制药厂(后来的昆药集团)则成为诺华的原料药供应商。
2001年4月,WHO建议在疟原虫对传统抗疟药物产生抗药性的国家使用青蒿素复方制剂,因为当时没有一家中国制药公司符合WHO的GMP,诺华生产的复方蒿甲醚成为唯一一个达到WHO认证标准固定计量复方制剂。
2002年,复方蒿甲醚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由此奠定了诺华在青蒿素药物市场上的地位。
直到2014年6月,桂林南药(复星医药控股)新建的注射用青蒿琥酯生产线(INJ-I)和小容量生产线(INJ-II)通过了WHO的PQ认证,国内药企方才之一次以独立的姿态走上了WHO面向全球的采购平台。
五、原料药市场:印度低价之争?
国内企业在青蒿素领域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原料药,全球原料药提供商主要来自于中国、印度等地。目前国内青蒿素原料药有11个批文,蒿甲醚原料药有8个生产批文。但主要的生产商为昆药集团(含孙公司重庆华方武陵山)、桂林南药。其中,昆药集团占国内市场份额约60%-70%。
近几年,由于原料药供过于求与印度企业的低价竞争,国内市场正在逐步萎缩。以蒿甲醚为例,我们估计目前全球蒿甲醚原料药的需求量在150吨左右,而仅中国地区的产能就有近200吨。
2013年中国蒿甲醚原料药出口量为32吨,出口额约3000万美元,仅占全球需求量的20%左右,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
除了来自印度等地区的低价竞争外,国内原料药厂商或还面临着来自化学合成领域的压力。2013年4月的《Nautre》报道中,海外科学家已成功运用合成生物学合成青蒿素,赛诺菲获许制造青蒿素的化学前躯体,该产品已于2014年8月上市。
尽管该产品目前还未大规模放量,但也意味着国内企业欲在青蒿素领域获得突破,就必须实现制剂的放量。
点击右边链接下载聪明投资者APP,更多精彩在等你!LinkedME
声明:凡注明“聪明投资者”的作品,版权均属聪明投资者。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违者必究。所有文章旨在记录和传递信息,不代表“聪明投资者”赞同或反对其观点。
2015 年 12 月 10 日,屠呦呦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证书、奖章、奖金等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2015 年 12 月 7 日,屠呦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报告厅发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演讲,讲述50年前,中国科学家在艰苦的环境下,从中医药中发现抗疟新药的故事。屠呦呦在介绍自己的研究之后,强调这不仅是授予她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她特别提到以“523任务”为中心的科研大协作,为青蒿素及青蒿素衍生物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从传统中药青蒿中分离出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由于其在治疗恶性疟和间日疟中表现出的高效、速效、低毒,以及与其他抗疟药物无交叉抗药性,已成为国际上广泛应用于治疗疟疾的首选抗疟药物,为解除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病痛作出了巨大贡献。
“523任务”——特殊时代的使命
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至今依然还是一个全球广泛关注且亟待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早在 1631 年,意大利传教士萨鲁布里诺(Agostino Salumbrino)从南美洲秘鲁人那里获得了一种有效治疗热病的药物——金鸡纳树皮(cinchona bark)并将之带回欧洲用于热病治疗,不久人们发现该药对间歇热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1820 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ierre Joseph)和药学家卡文托(Joseph BienaiméCaventou)从金鸡纳树皮分离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并将之命名为奎宁(quinine)。1944 年美国有机化学家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与德林(William Doering)之一次成功地人工合成奎宁。此后,科学家们对抗疟药不断改进,形成了以奎宁等为代表的芳、杂环甲醇类,以氯喹等为代表的 4- 氨基喹啉类,以及以阿莫地喹等为代表的杂环氨酚类抗疟药。这些抗疟药在人类防治疟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药物的大量长期使用,疟原虫的耐药性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20 世纪 60 年代初,恶性疟原虫在一些区域已经出现对氯喹的抗药性,尤以东南亚最为严重。当时,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抗氯喹恶性疟的侵袭困扰交战双方,导致作战部队大量减员。为此,美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研究疟疾,主要目标是寻找新型的抗疟药物。其中,美国华尔特 · 里德陆军研究所(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筛选了 20 多万种化合物。越南方面受条件所限,无力研制开发新药,于是请求中国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中方派出研究人员进行了近 2 年的现场调查以及实地救助,意识到疟疾防治的迫切性与复杂性。因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人民 *** 总后勤部于 1967 年 5月 23 日—5 月 30 日在北京召开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机构和有关省、直辖市、自治区、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大协作会议,并提出开展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的大协作工作。由于这是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为了保密起见,遂以开会日期为代号,简称“523 任务”。
“523 任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医药研究的之一个“大科学”研究计划。它具有多学科交叉、多机构合作、投入人力资金强度大等特点。为了落实任务规划,加强领导,当时国家组织成立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员有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 *** 总后勤部、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国家科委、 *** 总后勤部为正、副组长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事机构,以中国人民 *** 后字 236 部队(军事医学科学院)为主,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各派一名人员。办公室设在后字 236 部队,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与科研情况交流。
1967 年 6 月,领导小组向参加单位下发《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规划》,时间为 3 年;根据专业划分任务,成立化学合成药、中医中药、驱避剂、现场防治 4 个专业协作组,后来又陆续成立针灸、凶险型疟疾救治、疟疾免疫、灭蚊药械等专项研究的专业协作组。各专业协作组负责落实协作计划、进行学术与技术交流。
虽然规划对各项任务的安排和各单位的分工比较详细,但是任务执行时各单位之间的协作则会随着一些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当时中医中药、针灸防治疟疾研究小组组长单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组长单位为上海针灸研究所和后字 236 部队,1969 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加入。这个研究小组有3个研究项目,题目分别是“常山及其他抗疟有效中药的研究”“民间防治疟疾有效药物的疗法的重点调查研究”和“针灸防治疟疾的研究”,参与单位有近 20 家。该研究小组除发现青蒿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成果,如对常山乙碱的改造、从植物鹰爪和陵水暗罗中分离出有效抗疟单体鹰爪甲素和一种名为暗罗素的金属化合物等。尤其是在对鹰爪甲素进行化学结构研究中,发现其为过氧化物,这为后来研究并合成新抗疟药提供了思路,并且在确定青蒿素的结构过程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来自传统药物的发现
曲折的前期筛选工作
“523 任务”制定的《中医中药、针灸防治疟疾研究规划方案》第二项为“民间防治疟疾有效药物和疗法的重点调查研究”。该方案的备注中列出了根据文献调查提出的作为重点研究的药物,其中列有青蒿(排在第 5 位)。但是,在之后的记录中没有发现有关青蒿筛选的相关记载。根据蔡国定回忆,该方案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傅丰永教授拟定,原本准备作为常山之后的重点筛选对象,后因傅丰永、蔡国定均在“文革”中“靠边站”或者下放“五七干校”而中断。
1969 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军代表的建议下,“全国 523 办公室”邀请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中药所”)加入“523 任务”的“中医中药专业组”。北京中药所于1969 年 1 月接受“523 任务”,并指定化学研究室的屠呦呦担任组长,组员是余亚纲和郎林福。
1969 年 4 月,中医研究院革委会业务组编成了收集有 640 余方的《疟疾单秘验方集》。该验方集与当时其他文献类似,都是把与常山相关的验方列在最前面,其中第 15 页记载有青蒿,但并未对青蒿有特别的关注。
1970 年,“全国 523 办公室”安排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顾国明到北京中药所协助他们从传统中药中寻找抗疟药物。由于当时北京中药所的条件较差,筛选出的样品由顾国明送往军事医学科学院做鼠疟模型的研究。余亚纲查阅中医药文献,并且以 1965 年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出版的《疟疾专辑》为蓝本,进行整理分析后列出重点筛选的药物为: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他们共用水煎或乙醇提取,筛选了近百个药方,其中青蒿曾出现过对鼠疟原虫有 60%—80% 的抑制率,类似的结果有若干个。北京中药所档案显示,从 1970 年 2 月开始,屠呦呦小组一共送了 10 批 166 种样品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检测,每一种样品都有相应的抑制率。其中,前 3 批样品大部分没有药物名称,只有溶剂提取物名称,主要溶剂为乙醇、乙醚、石油醚;第 4 批样品后面有特别注明“屠呦呦筛选”,同样没有具体药品名称,主要为一些酸性或碱性成分加水;从第 5 批样品开始均未有特别注明,但都写明了药物名称;第 8 批中最后一个药物为雄黄,抑制率为 100%;第 9 批中也出现了几次雄黄,抑制率均在 90% 以上;青蒿出现在第 10 批样品中,抑制率显示为 68%,其提取溶剂为乙醇。这个结果与余亚纲的回忆一致:他在筛选过程中雄黄的抑制率曾有过 100%,青蒿的抑制率没有雄黄高,但考虑到雄黄为三氧化二砷类化合物,不适宜在临床上使用,因此退而求其次考虑抑制率排在其后的青蒿。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余亚纲因有其他任务调离研究小组,北京中药所因人力不足,打算下马该研究,研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发现并命名青蒿素
1971 年 5 月 21 日—6 月 1 日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领导小组改为由卫生部(正组长)、总后卫生部(副组长)、化工部和中国科学院三部一院领导。会上,北京中药所提出下马不干的想法,但未获得卫生部的批准。会后,北京中药所重新组织了研究小组,屠呦呦仍任组长,与组员钟裕蓉继续提取中药,郎林福和刘菊福做动物试验。屠呦呦曾表明“经过 100 多个样品筛选的试验研究工作,不得不再考虑选择新的药物,同时又复筛过去显示效价较高的中药。因为青蒿曾出现过 68% 的抑制率,后来对青蒿进行复筛,发现结果不好,只有 40% 甚至 12% 的抑制率,于是又放弃了青蒿”。根据北京中药所的药物筛选记录,1971 年 7 月 26 日筛选(序号 16)青蒿抑制率 12%,9 月 1 日(序号 114)青蒿醇抑制率 40%,10 月 4 日(序号 191)青蒿乙醚抑制率达 100%。不过,档案中的药物筛选记录显示:1971 年 7—12 月,10 月 4 日 191 号青蒿乙醚提取物首次出现 99% 的抑制率,第 201、205、277、278、281、307、345、347 等均为青蒿的样品,抑制率都在 99% 及以上。刚开始的筛选结果并不太稳定,也有用其他溶剂提取的,抑制率都不高,12 月 6 日之后筛选的结果相对稳定。
1972 年 3 月 8 日,屠呦呦作为北京中药所的代表,在“全国 523 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作题为《用 *** 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工作》的报告,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达 100% 的结果,引起全体与会者的关注。资料显示,复筛时屠呦呦从本草和民间的“绞汁”服用的说法中得到启发,考虑到有效成分可能在亲脂部分,于是改用乙醚提取,这样动物效价才有了显著提高,使青蒿的动物效价由 30%—40% 提高到 95% 以上。屠呦呦更先提取出对鼠疟原虫具有 100% 抑制率的青蒿乙醚中性成分,成为整个青蒿素研发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同时也开启了其他单位研究青蒿素的大门。
从 1971 年 1月起,屠呦呦小组开始大量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并于当年 6 月底完成了狗的毒性试验。为了能尽快开展临床试验,在当年对青蒿乙醚提取物对狗的毒性试验结果尚存在一定争议的同时,6—8月期间,屠呦呦、郎林福、岳凤仙与章国镇、严述常、潘恒杰、赵爱华、方文贤先后以不同剂量分作两批进行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部分的自体试服,均未出现明显的毒副作用。在经过多次讨论以后,1972 年 8月,屠呦呦带队在海南岛开展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疗效试验。期间,倪慕云设计了色谱柱分离的前处理,使青蒿乙醚提取物中性部分的抗疟作用再次得到提高。钟裕蓉从文献获知硅胶柱分离中性化合物更有效,于是便与助手崔淑莲在倪慕云柱前处理的基础上,按文献提供的 *** 用硅胶柱层析,石油醚-乙醚(后改为石油醚-乙酸乙酯)梯度洗脱,分离乙醚中性提取物。1972 年 11月8日,改用上海试剂厂生产的硅胶柱分离,然后用石油醚和乙酸乙酯-石油醚(不同比例)多次洗脱。更先获得少量的针状结晶,编号为“针晶Ⅰ”(No.1 或针 1);随后洗脱出来的是针状结晶,编号为“针晶Ⅱ”(No.2 或针 2);再后来得到的另一种方形结晶,编号为“结晶Ⅲ”(No.3 或方晶)。当时结晶的叫法比较多,并没有统一。同年 12 月初,经鼠疟试验证明,“针晶Ⅱ”是唯一有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此后,北京中药所向“全国 523 办公室”汇报时,将抗疟有效成分“针晶Ⅱ”改称为“青蒿素Ⅱ”,有时也称青蒿素,两个名字经常混着用。再后,北京中药所均称“青蒿素Ⅱ”为青蒿素。
黄花蒿素与黄蒿素的相继发现
参加南京会议的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研究人员回山东后,借鉴北京中药所的经验,用乙醚及酒精对山东产的黄蒿进行提取,经动物试验,获得较好的效果,并于 1972 年 10 月 21日向“全国 523 办公室”作了书面报告。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在实验结果中指出:黄花蒿的提取物抗鼠疟的结果,与北京中药所青蒿提取物的实验报告一致。此后,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协作,1973 年 10 月开始做有效单体的分离。当年 11月,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从山东省泰安地区采来的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中分离提取出 7 种结晶,其中第 5 号结晶命名为“黄花蒿素”,具有抗疟作用。
1972 年底,云南“523 办公室”副主任傅良书到北京参加每年一度的地区“523 办公室”负责人会议,得知了北京中药所青蒿研究的情况。他回去后召集云南药物所的有关研究人员开会,通报了这一消息,并提出利用当地植物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对菊科蒿属植物进行普筛。1973 年春节期间,罗泽渊在云南大学校园内发现了一种一尺多高、气味很浓的艾属植物——“苦蒿”,当下采了样本,带回所里晒干后进行提取。结果发现“苦蒿”的乙醚提取物有抗疟效果,复筛后结果一样。他们边筛选边提取,当年 4 月,罗泽渊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苦蒿结晶Ⅲ”,后改称为“黄蒿素”。
青蒿素的结构测定
1973 年初,北京中药所开始着手对青蒿素Ⅱ进行结构测定,由于他们的化学研究力量和仪器设备薄弱,结果不太理想。他们了解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有机所”)的刘铸晋对萜类化合物的研究有较多经验,于是派人与有机所联系,希望协作进行“青蒿素Ⅱ”的结构测定。为此,屠呦呦于1973 年 8 月下旬携带有关资料到有机所联系青蒿素结构测定事宜。刘铸晋因有其他工作而将青蒿素结构测定工作交由周维善组。自 1974 年 2 月到 1976 年间,北京中药所先后派出倪慕云、钟裕蓉、樊菊芬和刘静明到有机所参与结构测定工作。她们在上海做实验的同时及时将进展告诉在北京的屠呦呦等,屠呦呦等通过向林启寿、梁晓天等请教、沟通,再将意见汇总反馈给上海的工作人员,为上海进行的结构测定工作提供参考。
屠呦呦等于 1975 年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取得联系并开展协作,用当时国内先进的 X 衍射 *** 测定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完整、确切的青蒿素结构最后是由生物物理所的 *** 飞、梁丽等在化学结构推断的基础上,利用生物物理所的四圆 X 射线衍射仪,测得了一组青蒿素晶体的衍射强度数据。研究人员采用一种基于概率关系而从衍射强度数据中获取相位数据的数学 *** ,利用北京计算中心计算机进行计算,在 1975 年底至 1976 年初得到了青蒿素的晶体结构;后经梁丽等在精细地测定反射强度数据的基础上,确立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
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与当时已知的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分子中有 7 个手性中心,包含有 1,2,4-三噁烷的结构单元以及特殊的碳、氧原子相间的链。
全国范围内的青蒿素临床验证及其他工作
1973 年上半年,为争取当年秋季进行临床验证,北京中药所在提取设备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向研究团队增派蒙光荣、谭洪根等人,并从中医研究院临时借调数名进修人员进行提取。研究人员带上所里分离获得的青蒿素Ⅱ100 多克,于当年 9 月赴海南开展临床验证,一共做了 8 例临床,其中恶性疟 5 例、间日疟 3 例。结果显示,青蒿素对间日疟有效,但是未能证明对恶性疟的效果。
山东省黄花蒿协作组 1974 年 5 月中上旬在山东巨野县城关东公社朱庄大队用黄花蒿素对 10 例间日疟患者进行临床观察,效果很好。
1974 年 9 月8日,云南临床协作组的陆伟东、王学忠带着黄蒿素到云县、茶坊一带进行临床效果观察。10 月13日他们在耿马碰到广东中医学院的李国桥率医疗队在耿马开展脑型疟的救治以及“7351”的临床验证等工作。经北京和云南地区“523 办公室”领导的同意,陆伟东提供药给李国桥小组一起进行临床验证 。云南小组的成员于 11 月5日返昆明。到当年年底,广东医疗队共验证了18 例,其中恶性疟 14 例(包括孕妇脑型疟 1 例、黄疸型疟疾 2 例)、间日疟 4 例。汇集之前云南协作组验证的 3 例患者,云南提取的黄蒿素首次共验证了 21 例病人,其中间日疟 6 例、恶性疟 15 例,全部有效。所以,此次试验明确了黄蒿素对恶性疟疾的效果。
1975 年 2月底,在北京召开各地区“523 办公室”和部分承担任务单位负责人会议。广东地区“523 办公室”把广州中医学院在云南耿马临床试验的《黄蒿素治疗疟疾 18 例小结》在会议上进行了汇报。鉴于1972 年以来青(黄花)蒿实验研究的情况,尤其是黄蒿素在云南治疗恶性疟取得的良好疗效,青(黄花)蒿素被列入1975 年“523 任务”的研究重点。会议之前,卫生部时任负责人刘湘萍听取汇报,对北京中药所的工作因青蒿研究挫折又一次准备下马提出了批评 。北京中药所 1973 年下半年到 1974 年下半年在提取青蒿素工作方面遭遇较大的挫折。1975 年 4 月,在成都召开了“523 任务”中医中药专业座谈会。由于前一年李国桥等用黄蒿素治疗恶性疟取得了良好效果,制定了当年的研究计划,开始进行全国大会战扩大临床验证,参加青蒿及青蒿素研究的单位和人员大量增加。为了统一临床诊断及验证标准,在下现场之前,“523 办公室”在海南组织李国桥等专家对参与临床验证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疟原虫观察 *** 、体温测定时间等相关知识的培训。截至 1978 年 11月青蒿素(包括黄花蒿素、黄蒿素)治疗疟疾科研成果鉴定会时,参与青蒿及青蒿素研究和协作的单位有 45 家之多。这些单位用青蒿粗制剂、青蒿素共进行了 6 555 例的临床验证,用青蒿素制剂治疗的有 2 099 例,其中恶性疟 588 例(含脑型疟 141 例)、间日疟 1 511 例。
各研究单位在青蒿素的药理、毒理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开展了青蒿素的含量测定研究。1977年 2 月,“全国 523 办公室”在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举办之一次青蒿素含量测定技术交流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除北京中药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外,还有上海、广东、广西、江苏、河南、四川、湖北等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关的药物研究所、制药厂等 15 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同年 9 月,在北京中药所举办第二次青蒿素含量测定技术交流学习班,邀请了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严克东指导,以南京药学院和广州中医学院建立的紫外分光度法为基础,经过集体讨论改进了操作 *** ,并在不同的仪器上比较其测定误差以后,一致认为这个 *** 的特异性、精密度和准确度都符合青蒿素原料药和制剂的测定要求,也便于基层药检部门执行。最后由广州中医学院沈璇坤、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严克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罗泽渊、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田樱、北京中药所曾美怡共同完成的《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青蒿素含量》文稿于 1983 年公开发表。青蒿素质量标准则是以北京中药所曾美怡起草的质量标准为主,参考云南和山东两单位起草的内容,共同整理制订出全国统一的青蒿素质量标准。
进一步改造青蒿素
大量临床结果证明青蒿素对疟疾具有速效、低毒的特点,但是用后其“复燃率”很高,而且只能口服。为解决青蒿素生物利用度低、复燃率高以及因溶解度小而难以制成注射剂液用于抢救严重病人的问题,“全国 523 办公室”根据当时各承担“523 任务”单位的技术设备和研究力量等实际情况考虑,于 1976 年 2 月将青蒿素结构改造的任务下达给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
上海药物所接受任务后,将合成化学室、植物化学室、药理室的“523 研究小组”作了具体分工。合成组负责青蒿素结构小改造(李良泉、李英负责);植化组负责青蒿素结构大改造和代谢研究(陈仲良负责);药理组负责结构改造化合物的动物筛选(瞿志强负责)。合成组在已有的青蒿素化学反应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化学结构和抗疟活性关系的研究。他们发现青蒿素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的必需基团;还发现双氢青蒿素的效价比青蒿素高 1 倍。由于双氢青蒿素的分子中存在半缩醛的结构,性质不够稳定,而且溶解度也未见改善,李英等又从双氢青蒿素出发合成了它的醚类、羧酸酯类和碳酸酯类衍生物。顾浩明等通过动物试验,发现几十个衍生物的抗疟活性几乎都高于青蒿素;其中, *** 224(后命名为“蒿甲醚”)的油溶性大、性质稳定,抗疟活性是青蒿素的 6 倍,因而被选中为重点研究对象。陈仲良等对蒿甲醚的生产工艺进行了研究,发展了用硼氢化钾替代硼氢化钠的一步法工艺。1978 年 7—9 月,在完成药学、药理、药代、药效、毒理、制剂等实验研究后,领导小组批准蒿甲醚在海南岛进行首次临床试验。该次试验由广州中医学院“523 临床研究小组”负责,上海药物所的顾浩明、朱大元将临床用药送到海南岛并参加了临床观察。临床试验证明疗效很好,为扩大临床试验,在“全国 523 办公室”的协调下,云南昆明制药厂承担了试制蒿甲醚的任务。1980 年初夏,朱大元等到昆明制药厂参与扩大中试。昆明制药厂完成蒿甲醚及其油针剂的试产任务,为蒿甲醚大规模临床试验提供了全部用药。
1977 年 5月,“全国 523 办公室”在广西南宁召开“中西医结合防治疟疾专业座谈会”。上海药物所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青蒿素衍生物的合成和抗鼠疟效价。会后,在广西化工局一位总工程师的建议下,桂林制药厂参与到青蒿素结构改造的研究工作中来。1977 年 6 月,桂林制药厂刘旭参加“全国 523 办公室”在上海召开的疟疾防治研究合成药专业会议。上海药物所的代表盖元珠、瞿志祥等报告了 *** 224 等青蒿素衍生物的合成、筛选结果和青蒿素结构改造计划。回厂后,刘旭立即进行青蒿素衍生物的合成。先在青蒿素的还原反应中,将该厂已有的原料硼氢化钾成功替换为硼氢化钠。同年 8 月,刘旭等设计合成了10 多个青蒿素衍生物;其中双氢青蒿素的琥珀酸半酯在鼠疟筛选中抗疟效价比青蒿素高 3—7 倍,可生成溶于水的钠盐,用于制备水溶性静脉注射剂,是救治重症疟疾的速效、方便使用的剂型。
除了蒿甲醚与青蒿琥酯,还有一个开发成药的青蒿素衍生物是双氢青蒿素。虽然北京中药所在 1974 年做青蒿素结构测定时得到过双氢青蒿素,但是真正明确双氢青蒿素的结构是在 1975 年底经生物物理所确证了青蒿素的结构以后。
1976 年,上海药物所在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中,就发现双氢青蒿素对鼠疟的抑制效价比青蒿素更强。但由于其稳定性差和溶解度较低等问题,上海药物所选择了更好的蒿甲醚。1990 年,北京中药所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单位讨论,认为双氢青蒿素是蒿甲醚和青蒿琥酯的体内活性代谢产物,而且生产成本较低,可以作为开发对象。于是启动了对双氢青蒿素的抗疟药理、毒理和安全性的评价,后由广州中医学院进行临床试验,先后在海南岛收治恶性疟患者 349 例。其中,7 天疗程总剂量 480 毫克治疗了 239 例,观察 28 天后,发现治愈率达 97.5%,结果表明双氢青蒿素具有良好的抗疟效果。
20 世纪 80 年代初,青蒿素类单药(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问世不久,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对恶性疟表现出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治疗效果,但3—5天疗程杀虫不彻底,易复燃,在长期广泛使用单药时可能会使疟原虫较快产生抗性。
拓展青蒿素与其他化学药的组方
1982 年下半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周义清和滕翕和向中国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指导委员会提出“合并用药延缓青蒿素抗性产生的探索研究”立题申请,得到批准,并提供启动经费。过去复方组方思路是组成药物之间的作用应该是协同增效,代谢半衰期相似。邓蓉仙、滕翕和组织自主研发的本芴醇(也是“523 任务”期间的成果之一)与青蒿素组方,并和青蒿素与周效磺胺-乙胺嘧啶配伍进行比较。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科研人员进行了相应的药理、毒理等实验研究之后,发现这种组方既显示出速效的特点,又有治愈率高的优点。最后经过鼠疟、猴疟的各种实验之后发现蒿甲醚和本芴醇 1 : 6 配比适宜,并于 1992 年完成了全部研究工作;当年通过新药审评,获得了复方蒿甲醚片新药证书和新药生产批件,由昆明制药厂生产。
为了进一步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延缓抗药性的产生,我国科学家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523 任务”期间或之后化学组研究人员研发的新化学抗疟药配伍,不仅发明了蒿甲醚本芴醇复方(coartem),还有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复方(artekin)、青蒿素磷酸萘酚喹复方(arco)、复方哌喹片(CV8)、青蒿素-哌喹片(artequick)等。至今,这些研究还在继续。
青蒿素类抗疟药组成复方或联合用药(ACTs),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定为全球治疗疟疾必须使用的唯一用药 *** 。利用青蒿素类药复方加服小剂量的伯喹治疗现症病人以阻止疟疾传播的技术,也被 WHO 确认和推荐。这些都是我国从事“523 任务”和青蒿素研究人员的创新。
中国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及其国际化
在 WHO 时任总干事 *** (H. Mahler)博士的倡议下,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署赞助的第四次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SWG-CHEMAL)会议于 1981 年 10 月6—10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会上,中方宣读了 7 篇研究报告;在分组讨论时,外国专家就相关专题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双方同意按照会议报告中的内容进行合作,在化疗科学工作组规划范围内制订有关研究计划,以便使这些药物最终能应用于将来的疟疾控制规划。1981 年 10 月 12 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研究机构与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之间在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的合作”会谈,指出中国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方面的资料不足;会谈还探讨了合作研究的优先计划,目的是为中国对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进行可能的国际注册打下基础。会谈提出“中国官方将在国内成立一个小型的指导委员会,目的为了履行规划和保证有效的组织协调”。
1982 年 1 月5—8日,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在北京召开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攻关协作会议,依据的是卫生部与 WHO 在 1981 年 10 月关于开发青蒿素类化合物作为新的抗疟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会谈的精神,制订 1982—1983 年的研究攻关计划,确定研究的目标与重点为“按照国际新药注册标准要求,优先完成青蒿酯钠水注射剂、蒿甲醚油注射剂和青蒿素口服制剂的临床前药理毒理实验资料,为进一步实现三药商品化和国际注册确立基础”;同时,会上提出了成立研究指导委员会。参会的有中医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上海药物所以及广东、广西、云南、山东等省区有关科研、院校、药厂的代表共 50 余人。在这次会上,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称“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基本成立,并且明确了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在会上,特别强调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科研成果是集体的成果,同时对后来的研究提出了 2 点要求。
关于统一归口问题。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有关协作的日常工作由中医研究院牵头负责,遇有重大问题必须报请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审批。它的一切科研成果都是全国多部门、多单位长期共同努力协作的结果。为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在工作中,凡需向 WHO 或国外提供有关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资料、原料、制剂,以及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谈判等,均由卫生部外事局统一归口,根据情况由卫生部外事局与有关部门或单位协商处理,或报请上级批准。
要继续发扬全国一盘棋和大协作的精神。会议认为要做好与 WHO 的技术合作,首先是做好我们国内的协作。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为我国首创药物,但要真正把这些新药达到国际注册标准,进入国际市场推广应用,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所能办得到的,必须依靠全国大协作和各部门、各单位共同支持,提倡全国一盘棋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攻关。
1982 年 2月1—14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建的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TDR)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SWG/CHEMAL)秘书 Trigg 博士,药物政策顾问 Heiffer 博士(美国华盛顿华尔特里德军事医学研究所药物科主任),毒理学专家 Cheng Chun Lee(李振钧)博士(美国有害物质环境保护办事处顾问)来华访问上海、北京、广州和桂林,同意从中方提出的合作计划中选出 7 个项目上报 SWG/CHEMAL,并就预期在 2 年内的开发研究项目、技术要求、资助问题,以及提请WHO 考虑的培训计划(5 名人员出国学习和举办药代动力学和药物代谢培训班)和到泰国进行青蒿酯钠临床试用等问题,初步达成了共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 WHO 的合作之间未能得以继续。1983 年TDR/CHEMAL 推荐华尔特 · 里德陆军研究所与中国的合作,不过经过了 2 年多的谈判,最终不了了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于对国外药品注册信息了解不多以及国外生产厂商的种种担心和国内药物生产标准还不能符合国际标准等种种原因,国内抗疟药打入国际市场成了一个难题。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科研人员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努力下,1989 年上半年由国家科委牵头,会同国家医药总局、卫生部、农业部和经贸部共同召开了“关于推广和开发青蒿素类抗疟药国际市场”的工作座谈会,周克鼎以前“全国 523 办公室”秘书和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的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会上,他详细阐明了相应的方案,并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可。会议决定抗疟药国际开发归口国家科委负责,从此推广和开发青蒿素类抗疟药国际市场工作在国家科委领导下统一对外。1989 年下半年,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分别与中信技术公司等国内大型国有外贸公司签订了《开拓青蒿素类抗疟药国际市场合同》。在多方的努力以及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1994 年 9月20日CIBA-GEIGY(瑞士汽巴嘉基公司,现瑞士诺华公司的前身之一)和中方的《许可和开发协议》(Licence& Development Agreement)正式签署,10 月 17 日得到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的批准。1994 年 12 月 2 日双方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中瑞双方合作研制开发新一代青蒿素系列抗疟药”。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摸索与努力,中国的药品终于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这也是中国之一个自主研发打入国际市场的药物。
结语
1967 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 *** ,大多科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由于“523 任务”是一项国家的战备任务,所有的参研单位和人员都奉命而行,因此这项任务能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排除一些干扰,比较顺利地展开。这项任务既服务于国家外交和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新药研发。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国家需要与科学研究互动的典范。青蒿素研制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多番周折。在当时中国科研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比较差的环境下,通过协作攻关,成功研制出抗疟新药——青蒿素,成为世界抗疟药研究的奇迹。
青蒿素研究是一个典型的任务带动科研和学科发展的案例。青蒿素研制集中了国内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不长的周期内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于此同时,“523 任务”也培养了一大批抗疟药物研究的科研骨干。“523 任务”获得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复方已成为当今全球重要的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现被誉为 20 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作者:黎润红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屠呦呦团队青蒿素研究获新突破 应对抗药性需更多新药6月17日上午,新华社报道了屠呦呦及其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此前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研究显示,传统的对疟疾感染者采用的青蒿素联合疗法(“青蒿素药物”联合“其他抗疟配方药”疗法),面临着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疾病治疗效果下降的挑战。屠呦呦团队最新研究的突破在于,通过适当延长用药时间,以及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能够有效提高对疟疾感染者的治疗效果。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多款能与青蒿素药物搭配使用的其他抗疟配方药。不过,更换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就需要更多的新药。
联合疗法为抗疟主流 ***
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介绍,疟疾是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威胁生命的疾病,通过受感染的雌蚊叮咬传至人类。2017年,全球有2.19亿例疟疾病例,并被估计有43.5万例疟疾死亡病例。非洲是疟疾高发地,2017年占全球疟疾病例总数的92%。
“这个病(疟疾感染)挺可怕的。”浙江某高校赴坦桑尼亚汉语志愿者小郑(化名)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出国前,我们都接受了体检,还给我们都发了青蒿素(复方双氢青蒿素片)。不过老队员还是推荐我们购买一些非洲当地销售的其他抗疟药物,有备无患。”小郑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来一张包含四款非洲在售的抗疟药的图片,分别是诺华的Coartem、印度Strides Arcolab公司的Combiart、印度Cipla公司的Lumartem和华立科泰的DUOCOTECXIN(科泰复)。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诺华及两家印度制药公司的产品,药物成分均为Artemether/Lumefantrine(蒿甲醚、苯芴醇)。与此同时,在这三款药品的包装上,都有一个配以文字“ACTm”的绿色树叶标志。ACT(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y)即“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截至2016年底,已经把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作为一线治疗 *** 的国家有80个,国际采购的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ACT)的疗程总数估计为4.09亿个。
应对抗药性需更多新药
记者注意到,虽然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ACT)目前是世界范围内治疗疟疾感染最有效的手段。但世界卫生组织提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绝对不能用于单一口服疗法,因为这有可能引起对青蒿素的耐药性。
在小郑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供的非洲当地在售抗疟药品图片中,华立科泰DUO-COTECXIN(科泰复,双氢青蒿素哌喹片)是唯一的中国药企产品,该药上市多年,用于治疗非重症恶性疟及间日疟,目前已被昆药集团(600422,SH)收购。除此之外,昆药集团还拥有另一抗疟药——复方磷酸萘酚喹片。
屠呦呦及其团队最新研究发现,适当延长用药时间,由三天疗法增至五天或七天,以及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治疗疟疾感染立竿见影。
显然,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就需要更多的新药。但目前,国内众多“青蒿素概念股”公司中,极少有公司在抗疟疾新药研发上发力。新和成(002001,SZ)、华润双鹤(600062,SH)、白云山(600332,SH)仅仅是拥有双氢青蒿素制剂批文。而浙江医药(600216,SH)则生产抗疟疾类医药原料药,是诺华Coartem的供应商。
(责任编辑:李嘉玲)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科泰复(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世卫预认证资助的公告证券代码: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116号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公司”)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签署“昆药科泰复(双氢青蒿素哌喹片)世卫预认证资助”协议,鉴于昆药集团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青蒿素及其成品制剂全产业链生产商,并一直以来致力于青蒿素产品国际化推广和全球人类抗疟事业发展,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决定根据项目进展分批次向昆药集团资助共计1,251,532.00美元,帮助公司的科泰复产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以下简称“世卫认证”),使昆药集团成为符合世卫质量标准的双氢青蒿素哌喹片全球采购的供应商。除给予资金补助外,基金会还将通过其全球范围内的专家资源向昆药持续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昆药集团进行产品技术攻关及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以顺利达成世卫认证。
此项资金将用于基金会&昆药集团合作对科泰复产品作为抗疟药进行世卫认证申报,资金仅可用于支付上述项目开展所产生的费用,公司在收到上述资金时,将按照基金会的指定用途进行使用。在基金会的帮助下,公司科泰复产品的国际质量标准将得到大力提升,预期将加速公司科泰复通过世卫认证的进程。通过世卫认证后,公司将成为抗疟药公立市场采购的主要参与者,在未来的市场周期可大幅提高科泰复销售额。同时,昆药集团在该项目所获得的相关技术经验也将为后续其他品种的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
此项资助可减少公司对科泰复产品世卫认证的支出,对公司当期损益无重大影响,资助的具体获取金额及获取时间需根据公司科泰复产品世卫认证工作进展及各项工作完成情况予以确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消除疟疾“中国神草”青蒿素功不可没4月25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说起疟疾,人们自然会想到青蒿素和它的发现者屠呦呦。
今年恰逢青蒿素问世50周年。曾经,人们谈“疟”色变,有数字显示,在青蒿素被发现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100万人死于该病。
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从20世纪40年代每年报告约3000万疟疾病例到如今完全消除,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而在全球,目前仍有91个国家和地区有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占全球比例的90%。但自2000年以来,全球疟疾死亡率已经下降了一半。其中,“中国神草”青蒿素功不可没。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自20世纪70年代青蒿素问世以来,所治愈的疟疾患者不计其数。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疟疾肆虐地区的救命药。
“这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呦呦说。
在中国乃至全球,屠呦呦和青蒿素的故事家喻户晓。半个世纪以来,青蒿素、双氢青蒿素、复方蒿甲醚、双氢青蒿素哌喹片……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在抗疟临床得到广泛应用,并走出国门,最终影响了世界。
而屠呦呦却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青蒿素是举国体制的结果,在全球疟疾防治的战场上,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有组织有目标的大团队作战才能逐步战胜疟疾。”
屠呦呦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也认为,青蒿素的发现,体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医药在国际医疗健康领域中的一项原创,更折射出一代中国科研人员的精神风貌,那就是他们对于国家任务的责任与担当。
“现在这种精神已经被总结成‘青蒿素精神’:胸怀祖国、敢于担当,团结协作、传承创新,情系苍生、淡泊名利,增强自信、勇攀高峰。” 廖福龙说。
青蒿素抗药性和其他适应症研究取得进展
毋庸讳言,历经半个世纪,青蒿素对全球疟疾防治功不可没,但其治疗疟疾的深层机制仍模糊不清。尤其是青蒿素的抗药性,是屠呦呦一直关心的问题,也是全球抗疟面临的更大挑战。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屠呦呦和团队成员一直在努力。“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找出青蒿素作用机理,破解其耐药性,以及如何扩大青蒿素类药物的适应症。”廖福龙说。
欣喜的是,2019年6月17日,屠呦呦团队对外公布,其青蒿素抗药性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刚,采用化学生物学 *** ,研究血红素激活青蒿素的过程,发现激活的青蒿素可与疟原虫的100多种蛋白以共价键结合并使之烷基化,破坏疟原虫的诸多生命过程,从而杀死疟原虫。这个血红素激活的多靶点学说已得到国际抗疟学界的认同,对揭示青蒿素抗疟的深层机理、耐药现象并促进更有效的临床用药等意义重大。
王继刚介绍,根据研究,青蒿素在人体内半衰期很短,仅1至2小时,而临床推荐采用的青蒿素联合疗法(ACT)疗程为3天,青蒿素真正高效的杀虫窗口只有有限的4至8小时。而现有的耐药虫株充分利用青蒿素半衰期短的特性,改变生活周期或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以规避敏感杀虫期。同时,疟原虫对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抗疟配方药”也可产生明显的抗药性,使青蒿素联合疗法出现“失效”。
针对此,团队提出了新的应对治疗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由3天疗法增至5天或7天疗法;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合理和战略性地应用青蒿素联合疗法是应对治疗失败的更佳解决方案,也可能是唯一解决方案。”王继刚强调。
除了青蒿素抗疟研究之外,团队还十分关注青蒿素的抗癌等功效。青蒿素的抗癌机制与抗疟机制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相比于正常体细胞,肿瘤细胞中血红素的合成更加旺盛,从而激活了青蒿素或其衍生物,随后激活的青蒿素以多靶点方式杀灭肿瘤细胞。但团队成员表示,青蒿素的抗癌功效目前还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有效不等于可以成药。青蒿素能否成为抗癌药,还需要大量的后续研究工作。
再就是备受关注的有关青蒿素类药物治疗红斑狼疮问题。双氢青蒿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果独特。“在昆药集团主持下,目前正在开展二期临床试验,预计9月份可以揭盲。”廖福龙说,此前试验表明,青蒿素对治疗红斑狼疮存在有效性趋势。但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付丽丽)
来源: 科技日报
昆药集团: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尚处临床二期患者入组阶段中证网讯(记者吴科任)昆药集团(600422)6月17日晚公告,公司目前销售的青蒿素类产品用途均为疟疾治疗,且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公司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目前尚处于临床二期患者入组阶段,该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告显示,昆药集团在售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产品有:复方磷酸萘酚喹片、蒿甲醚片、蒿甲醚原料、蒿甲醚注射液、双氢青蒿素哌喹片。此类产品2018年营业收入为6925.92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比例仅为0.98%,营业利润为667.65万元。
昆药集团2016年9月8日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签订《双氢青蒿素片新适应症-红斑狼疮项目 *** 合同书》,以里程碑付款的方式,出资7000万元,向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购买其所持有的双氢青蒿素片新适应症-红斑狼疮研发项目临床前研究所取得的相关专利及临床批件。
昆药集团表示,目前,上述研发项目处于临床Ⅱ期患者入组阶段,这个药物研发项目还需要继续进行二期临床试验、后续还需要III期临床试验,以及药监局的注册审批程序。只有在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均表明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后,公司才可以向药监局(NMPA)提交新药注册申请。药物研发的二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及注册时间很长,而且在临床试验以及注册申请的过程中,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能否得到验证,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该项目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的风险。即使药物能上市销售,仍然面临专利保护到期,竞争品种抢占市场先机等系统性风险。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昆药集团收获两连板 董秘:双氢青蒿素片处临床二期试验受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影响,6月17日及18日,昆药集团(600422,SH)股价连续涨停。
18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昆药集团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徐朝能。其表示,目前双氢青蒿素片正处于临床二期试验过程中,二期试验预计在15家医院展开,目前已在9家医院进行,有19位患者自愿参与临床试验。但他也坦言,“短期内,满足这个疾病临床需求的药品可能很难研发出来。”
昆药集团在青蒿素领域布局已有几十年之久,如今拥有七个蒿甲醚系列产品品种,参与起草制定的5个蒿甲醚系列药品质量标准收载于国际药典标准,但青蒿素相关产品对昆药集团的业绩贡献很小。
一期试验效果安全有效
伴随着屠呦呦团队最新研究进展引发巨大关注,负责开展临床试验的昆药集团也火了一把。
双方的合作开始于2016年。彼时,昆药集团宣布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签订《双氢青蒿素片新适应症-红斑狼疮项目 *** 合同书》,将以里程碑付款的方式出资7000万元,购买该项目临床前研究所取得的相关专利及临床批件。
6月18日,昆药集团再度“一”字涨停。
徐朝能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双氢青蒿素片正处于临床二期试验过程中。对于已完成的临床一期试验效果评价如何?徐朝能回答了四个字,“安全有效”。
他还表示,该项目二期临床试验结束后需进行三期临床试验,以及通过药监局的药品注册审批程序,才能最终上市销售。临床试验预计还将进行7到8年,“屠老师(屠呦呦)的团队给我们预计的时间是,如果试验顺利,2026年左右药品能够上市。”
由于红斑狼疮在临床上尚无治愈 *** ,该项目一旦通过临床试验并通过注册审批,是否意味着患者将迎来治愈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盘状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希望?徐朝能表示:“可以这么预期,因为这个疾病的治疗 *** 目前可以说是完全空白的。”
但他表示,对于该药物一旦成功上市可能占有的市场份额及可能形成的利润,目前昆药集团并没有预估。
在17日晚的公告中,昆药集团也提示了投资风险,称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目前尚处于临床二期患者入组阶段,该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风险。
对此,徐朝能也坦言,产品最终能否试验成功现在并没有预测,“我认为,短期内,满足这个疾病临床需求的药品可能很难研发出来”。
刚得知青蒿素抗药性研究进展
实际上,昆药集团是青蒿素药物研发生产的早期参与者。
昆药集团官网信息称,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启动了一项代号523的项目,旨在研发一种新的抗疟疾药物。当时,昆药集团的前身昆明制药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企业,参与了此项研发工作。
1990年,昆药集团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携手联合研发蒿甲醚复方型抗疟特效药,形成A+B新复方,该组方是全球之一个ACT固定比例复方药,开创了ACT药物开发及应用的先河,昆药集团成为全球之一家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进行疟疾治疗 *** (ACT疗法)研究的企业。
目前,昆药集团拥有七个蒿甲醚系列产品品种,参与起草制定的5个蒿甲醚系列药品质量标准收载于国际药典标准。
但昆药集团青蒿素类药物的收入规模较小。根据其2018年年报,昆药集团在售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产品有复方磷酸萘酚喹片、蒿甲醚片、蒿甲醚原料、蒿甲醚注射液、双氢青蒿素哌喹片。此类产品2018年营业收入为6925.92万元,仅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0.98%,营业利润为667.65万元。要知道,昆药集团2018年营收达71.02亿元,净利润为3.36亿元。
近年来,昆药集团抗疟疾药物营收呈下滑趋势。2018年,其抗疟类药物营收同比下滑35.66%;毛利率为52.71%,同比增加12.23个百分点。
有行业人士分析称,近年青蒿素产品销售额下降,主要与销售地区疟疾感染率下降有关。据了解,疟疾的发生与卫生条件差有很大关联,因此青蒿素抗疟疾药物的销售市场主要为国外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
徐朝能也表示,目前公司青蒿素抗疟疾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市场。但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国内仅有两家企业拥有对海外销售青蒿素抗疟疾产品资格。
为破解“青蒿素抗药性”难题,屠呦呦团队提出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等应对方案,昆药集团是否计划生产新药?徐朝能暂时未给出答案,“我们也跟你们同一天(6月17日)知道屠老师的研究进展,是否研发新药要看与屠老师团队后续的沟通”。
相对于市场较为有限的抗疟疾药品,一旦昆药集团在红斑狼疮项目上取得突破,无疑可以走向全球市场。
西南证券发布的研报认为,我国红斑狼疮疾病治疗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价值,保守估计我国潜在患者人数达到100万人,相当于全球患者的五分之一,该产品适应症拥有较大市场潜力。
但面对长达七八年的研发期和可能存在的研发风险,市场的追捧似乎为时尚早。在该产品没有取得新进展或获批上市之前,遭遇辅助用药、中药注射剂等政策压力的昆药集团,业绩还略显疲态。每经记者 陈星 每经编辑 徐斐
但面对长达七八年的研发期和可能存在的研发风险,市场的追捧似乎为时尚早。在该产品没有取得新进展或获批上市之前,遭遇辅助用药、中药注射剂等政策压力的昆药集团,业绩还略显疲态。
(责任编辑:李嘉玲)
青蒿素问世50年,“抗疟”历程广东中医药不缺席今年是青蒿素问世的第50周年,也是中国获世卫组织认证完全消除疟疾的第二个年头。50年来,中国通过提供药物、技术援助、援建抗疟中心、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向全球积极推广应用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为全球疟疾防治、佑护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历程中,也有广东中医药贡献的一份力量。
4月29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广东省中医药局在穗召开广东青蒿抗疟情况媒体通报会,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锋表示,从《肘后备急方》为屠呦呦贡献研发灵感,到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率团队以身试“疟”验证药效,到青蒿素药物研发升级、青蒿产业化技术提升,到广东专家携中国防治策略方案援助世界多个国家地区,广东中医药人从未缺席;今后广东仍将继续加快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支持推进青蒿素控制疟疾项目实施,推动青蒿素防治疟疾策略研究,努力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广州中医药大学宋健平教授团队在多哥下乡帮助当地居民正确服药。
青蒿素灵感源于岭南 问世后广东专家力证实效
徐庆锋说,广东中医药人为青蒿素的发现及其有效性的证实作出了重要贡献。1700多年前,有“岭南医祖”之称的葛洪写下了著名的《肘后备急方》,留下了青蒿抗疟的最早记载,而这也直接启发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成功提取青蒿素,为人类抗击疟疾作出历史贡献。
随后在1967年,我国 *** 为研究抗疟特效药,启动“523”任务,中医药协作组在针灸和中药两个方向上进行探索。承担针灸治疗疟疾任务研究的,正是广州中医学院(即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李国桥教授带领的团队。在研究过程中,李国桥教授“以身试疟”,寻找疟原虫发育规律,留下了宝贵的之一手资料,为抗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药物升级攻克难关 研发第四代复方青蒿素
广东中医药一直在为青蒿素药物的研发升级努力攻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已有药物存在的药效时间短、服药时间长、患者依从性差等问题,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抗疟团队开展复方青蒿素药物的研发并不断升级,目前已研发出第四代产品。2004年至今,广州中医药大学与新南方集团共同组建广东青蒿抗疟团队,成功研制出第四代青蒿素复方-青蒿素哌喹片,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其具有高效、速效、低副作用与服药简便等诸多优点。
据悉,青蒿素哌喹片已在40个国家取得国际专利保护,在36个国家完成商标注册,已在全球26个疟疾流行国家上市销售,多年来已成为众多疟疾高度流行国家自由市场的主要抗疟药品。
宋健平教授团队在科摩罗下乡推动发药工作。
广东专家携中国方案援外抗疟 超2000万人次受益
1967年至今的50多年间,以李国桥教授、宋健平教授为代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抗疟团队,不间断地奋战在全球抗疟一线。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主任宋健平教授表示,复方青蒿素消除疟疾项目实施以来,疟区直接受益民众超过2000万人次,累计派出抗疟专家260余人次,在外累计工作超24590天,培训当地基层抗疟员超过10000人,专业技术抗疟员超600人。
项目将中医群体辨证观运用到疾病防控领域,形成了青蒿素复方“全民服药、群防群治、灭疟求本”的中国特色疟疾防治方案,快速遏制疟疾流行,大幅减少疟疾发病和死亡,科学回答了抗疟群体有效性、安全性、抗药性等问题。
广州中医药大学援外抗击疟疾专家郭文峰副教授连线现场。

在通报会现场,至今仍率团队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从事疟疾防治工作的广东中医药大学郭文峰副教授连线介绍了援助情况。据了解,广东专家团队创新性地将高疟区(疟疾高流行区)全民服药、群防群治同步清除传染源的策略拓展到疟疾低流行区,坚持以青蒿素复方群防群治清除传染源的策略,通过清除疟疾示范项目,示范区首次实现了连续8个月零疟疾报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疟疾流行水平得到大幅度降低。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周洁莹 通讯员:粤卫信、粤杏林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陈婷婷